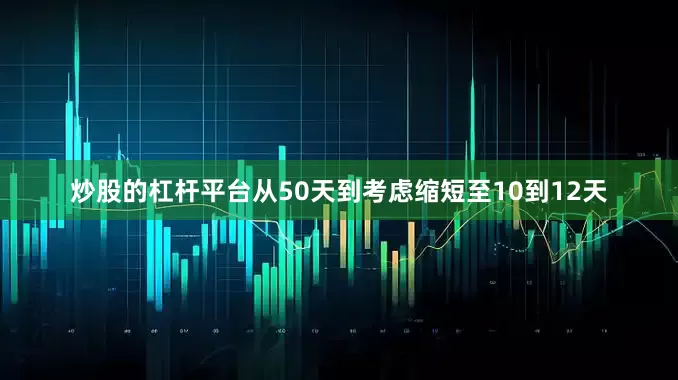画木莲花图寄元郎中
白居易
花房腻似红莲朵,艳色鲜如紫牡丹。
唯有诗人能解爱,丹青写出与君看。
唐郎中宅与诸公同饮酒看牡丹
刘禹锡
今日花前饮,甘心醉数杯。
但愁花有语,不为老人开。
一、意象选择与象征意蕴
白居易《画木莲花图寄元郎中》
诗中木莲花实为山荆子,生长于西南偏远之地,白居易任职忠州时发现其“花房腻似红莲朵,艳色鲜如紫牡丹”,以红莲之清雅、紫牡丹之华贵喻其形色,更赋予其超凡脱俗的品格。此花成为诗人自我写照:他因直言获罪贬谪江州,虽后提职忠州仍感仕途无望,木莲花“香酷似辛夷”却“长在深山野岭”,恰似其高洁志向与边缘处境的矛盾。画木莲寄友,既是对自然之美的传播,更是以花喻人,寄托“唯有诗人能解爱”的孤高心境。
刘禹锡《唐郎中宅与诸公同饮酒看牡丹》
展开剩余76%牡丹在唐代是盛世符号,刘禹锡笔下之花承载着中唐文人对功名与时代的追慕。“今日花前饮,甘心醉数杯”以宴饮之乐暗含对仕途顺遂的满足,而“但愁花有语,不为老人开”则借拟人化手法,道出对年华老去、盛世难再的隐忧。牡丹的“国色天香”在此成为时代精神的镜像,既呼应开元天宝年间“花开时节动京城”的狂热,又折射出经历“永贞革新”失败后的诗人对功名的复杂态度——既渴望如牡丹般绽放,又恐盛世已逝。
二、艺术手法与情感表达
白居易:以物观我,平易中见深意
白诗善用“多方比喻”与“侧面烘托”,如将木莲比作红莲、紫牡丹,既突出其形色之美,又暗含对主流审美(牡丹)的疏离。语言平易如话,如“丹青写出与君看”直白如日常对话,却饱含对知己的深情与自我价值的确认。其讽喻传统亦隐现于对木莲“超凡脱俗”的强调,暗讽京城士大夫对边地之美的漠视。
刘禹锡:以物观世,豪健中含哲思
刘诗以“对比”与“拟人”为核心,如《赏牡丹》中贬芍药为“妖无格”、芙蕖为“净少情”,以凸显牡丹“真国色”。此诗虽未直接描摹牡丹,但“但愁花有语”的拟人化想象,赋予花以人性,既写赏花之乐,更写对时光流逝的无奈。语言简练而意象丰赡,如“甘心醉数杯”看似洒脱,实则隐含对人生易老的慨叹,体现其“诗豪”特有的豁达与深邃。
三、文化语境与时代精神
白居易:个人际遇与士人心态
白诗中的牡丹意象折射中唐文人“外放与回归”的矛盾。木莲花作为边地奇花,经白居易推广而“名闻天下”,恰似其本人虽遭贬谪仍以文章传世。诗中“我寮展事,靡问文武”的自我期许,与“自比木莲”的孤高,共同构成中唐士人在仕途挫败中寻求精神超脱的典型心态。
刘禹锡:盛世追忆与功名焦虑
刘禹锡笔下的牡丹承载着对盛唐气象的追慕。中唐长安贵族竞相培育牡丹,赏花成为身份象征,刘禹锡参与其宴饮,既是对时代风尚的顺应,亦隐含对功名的渴望。然而“不为老人开”的忧惧,又暴露出其在“永贞革新”失败后,对政治机遇逝去的敏感。牡丹在此成为盛世与个人命运交织的符号。
四、 白居易与刘禹锡的牡丹意象,一者以边地奇花自喻,在平易中见孤高;一者以盛世国色寄情,在豪健中含哲思。白诗如木莲花,清雅而坚韧,根植于个人际遇的土壤;刘诗如牡丹,华贵而热烈,绽放于时代精神的天空。二者共同构成唐代牡丹书写的双璧,既见证了中唐文人“对盛世的追忆与现实的妥协”,更展现了诗歌意象在个人表达与时代精神之间的精妙平衡。
发布于:河南省瑞和网配资-炒股配资官网-怎么办理股票开户-网上配资平台配资门户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